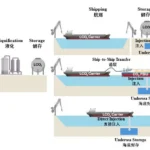分享文章
文/苦心草
新竹市長高虹安論文風波引發誣告官司,二審從判有期徒刑十月撤銷改判為六月,減刑判決對高而言不是寬典,反而像傷口撒鹽。因刑案獲不起訴再以誣告反制對造的案例不多,高虹安的有罪判決,法官敞開敗訴一方「復仇式」繼續爭訟的門扉,對司法絕非好事。

高虹安被自訴的誣告案,高不但沒有主觀犯罪,還有客觀上學位未撤銷的證據可資佐證。高無論在向檢察官「提告時」、「提告後」,在誣告案「一審時」、「二審時」四個時序,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論文始終存在是鐵一般的事,但法官視而不見。
退一步言,就算高虹安「提告後」論文被母校判定為抄襲,仍然缺乏高虹安「提告時」有誣告犯意的證據,原因無他,即高虹安認為她的論文著作是自創的、是沒有抄襲的。
依台灣高等法院新聞稿,合議庭得心證理由是「經調查證據結果,已證明被告明知其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論文內容大篇幅原文抄錄被告與資策會同事、指導教授合著之期刊論文,故本案事證明確」。
至於撤銷改判的理由,合議庭表示「被告行為固有不當,但自訴人指述『本案博士論文三分之二來自本案期刊論文』確實較誇張,且關於『與指導教授合謀』等評論則較為嚴苛,而被告事後有表示『減縮告訴範圍』,使自訴人所受損害有所減輕」等。
依法院見解,誣告案自訴人「確實較誇張」、「評論則較為嚴苛」不審究,反而去審究辛辛那提發給高虹安博士論文的權力,並進一步指「經調查證據結果」證明高虹安抄襲,法官審案有沒有越俎代庖?有沒有擴權?
刑事訴訟程序重於實體,是法律原則,程序方面包括管轄權與審判權,法官審理誣告案不從大方向著手結案,卻上綱「審判權」以致於擴權、凌駕在辛辛那提大學學術倫理之上,缺乏法律人應有的謙抑性格,已不言自明。
司法辦理誹謗案,考量的是加害人有無主觀犯意,誣告罪也一樣,要具備使他人受刑罰、懲戒犯罪故意被告才許論罪,兩種罪執法者都要視被告有無主觀犯意,這也是誣告案自訴人能從誹謗罪脫身的因素之一。
不過,法官在審誣告案時,卻選擇一條「最窄」的路去斷言高虹安的論文為抄襲,進而判誣告有罪,令人細思極恐;網路時代隔空叫囂者太多,壓垮司法量能的就是加重誹謗案,一旦告訴人提告被告無法成罪,告訴人隨即變成誣告犯且要承擔刑責,將讓有限的司法資源更難以喘息,法官判高虹安有罪,正式作出示範!(照片/翻攝高虹安臉書)